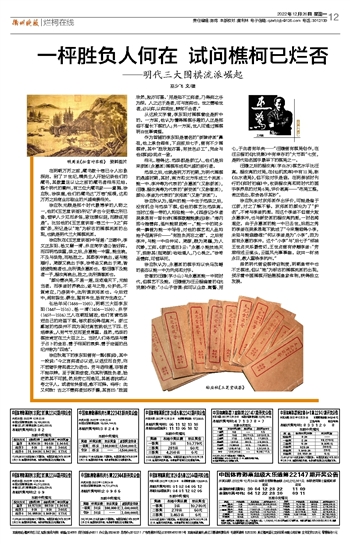巫少飞 文/摄
在明朝万历之前,藏书数十卷已令人印象深刻。到了17世纪,精英士人开始记录他们的藏书,其数量足以让之前的藏书者相形见绌。整个明代的衢州,有三位大藏书家——童珮、徐应秋、徐洪瑆,他们的藏书达“万卷”规模,这和万历之后商业印刷业的兴盛背景相关。
徐应秋无疑是那个时代最博学的人物之一,他的《玉芝堂谈荟》所记“多古今史载之所已备,惜学人少见而多怪,致往牒似诞,而疑诬用是”。比如他的《玉芝堂谈荟·卷三十一》之“弈棋”条,所记是以“地”为标志的围棋流派的出现,也就是明代三大围棋流派。
徐应秋在《玉芝堂谈荟》中写道:“正德中,李文正东阳、杨文襄一清、乔庄简宇诸公皆好弈。而四明范洪重,洪之后,永嘉鲍一中重,鲍生晚,不及与洪角,而格胜之。其郡李冲晚出,遂与鲍雁行。周源又晚出于李,徐希圣又晚出于周,皆骎骎角鲍者也,此所谓永嘉派也。婺汪曙不及鲍者一子,程汝亮晚出,胜之,此所谓徽派也。
“颜伦善决局,不差一道,足迹遍天下,无能当者。而李釜时养晚出,遂与之角,伦护名,不复肯应,乃游吴中,此所谓京师派也。今后进中,闽有陈生、蔡生,越有岑生,扬有方生鼎立。”
弘治年间(1488—1505),明朝三大臣李东阳(1447—1516)、杨一清(1454—1530)、乔宇(1457—1524)三人在朝廷辅政,他们常请范洪进自己的府里下棋,每次都玩得很高兴。浙江鄞城的范洪并不因为面对高官就低三下四、巴结奉承,人有气节反而更受尊重。显然,范洪的棋技肯定在三大臣之上。当时人们将范洪与善于占卜的金忠、善于相面的袁珙、善于绘画的吕纪并称为“四绝”。
徐应秋笔下的李东阳曾有一篇《棋说》,其中一段说:“今之言弈者必以适,以适反而自劳,则不若缩手旁观者之为适也。劳与适相遭,非智者不能卒辨。至于复图敛奁,则其所谓胜负者,始茫然其不可揽,然后劳亡而逸见,其甚者犹或以夸之乎人。或者怅怏郁结,愈不可释。呜呼!此又何哉?古之不善弈者如苏子瞻,其言曰:‘胜固欣然,败亦可喜。’用是知不工弈者,乃得弈之乐为深。人之达于是者,可与言弈也。世之善喻世者,必以弈,以弈观世,鲜有不合者。”
从这段文字看,李东阳对围棋看法是折中的。一方面,他认为懂得围棋乐趣的人正是那些不擅长下棋的人;另一方面,世人可通过围棋明白世事情理。
作为首辅的李东阳是著名的“茶陵诗派”鼻祖,他上承台阁体,下启前后七子,曾有不少围棋诗,其中“胜欣败亦喜,有技岂必工”,完全与他《棋说》观点一致。
相礼、楼得达、范洪都是浙江人,他们是后来浙派(永嘉派)围棋形成和兴盛的前行者。
范洪之后,也就是明万历初期,为明代围棋的鼎盛时期,其时,南方和北方形成三个流派:鲍一中、李冲等为代表的“永嘉派”(又称浙派),汪曙、程汝亮等为代表的“新安派”(又称徽派),颜伦、李釜为代表的“京师派”(又称“京派”)。
徐应秋认为,温州的鲍一中生于范洪之后,没有机会与范洪下棋,但他的棋艺比范洪高。当时江淮一带的人均知鲍一中,《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有一首长诗《围棋歌赠鲍景远》称:“海内即今推善弈,温州鲍君居第一。”鲍一中的同乡侯一麟曾为鲍一中写传,对他的棋艺和人品均给予很高评价——“有胜负两忘之德”。之后有李冲,与鲍一中伯仲间。周源,疑为周躔,为人沉静,工弈。《浙江通志》云:“永嘉小鲍技绝天下,独称其(指周源)咄咄逼人,乃心畏之。”徐希圣善弈,可惜早死。
徐应秋认为,永嘉派的棋手均以快马加鞭的姿态以鲍一中为先师和对手。
安徽的汪曙(字小山)与永嘉派鲍一中同时代,但棋艺不及鲍。汪曙曾为汪云程编著的《犹贤集》作跋:“小山子尝谓:弈可以企怠、寓警、用心,于此者有年矣……”汪曙曾有棋局创作,在汪云程的《犹贤集》中有幸存的“大节图”七变,是明代知名国手最早下的棋局之一。
汪曙之后的程汝亮(字白水)棋艺水平比汪高。程汝亮的对局,在《仙机武库》中有12局,称《白水遗局》,但不知对手是谁。在明崇祯时刊行的《弈时初编》中,收录程汝亮和同时代的国手李养泉的对局6局,评价甚高——“布局工整,奇正迭出,取舍各尽其妙”。
徐应秋未对京师派作出评价,可能是偏于江浙,对之了解不够。京师派的颜伦为了“护名”,不肯与李釜抗衡。而这个李釜不但曾大败永嘉李冲,也与新安派的程汝亮抗衡,一时名闻遐迩。由于永嘉派的鲍一中已去世,后起之秀的李釜在吴承恩笔下就成了“今来邂逅得小李,未知与鲍谁雌雄?”何以李釜是为“小李”,因为前有永嘉的李冲。这个“小李”与“后七子”领袖王世贞关系最密切,王世贞曾有诗赠李釜:“劳君相送云溪头,云里风光事事幽。欲共一杯消永日,教人重唤李杭州。”
虽然明代曾设棋待诏制度,明朝皇帝中也不乏棋迷,但以“地”为标志的围棋流派的出现,预示着中国围棋开始摆脱皇家体制,获得独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