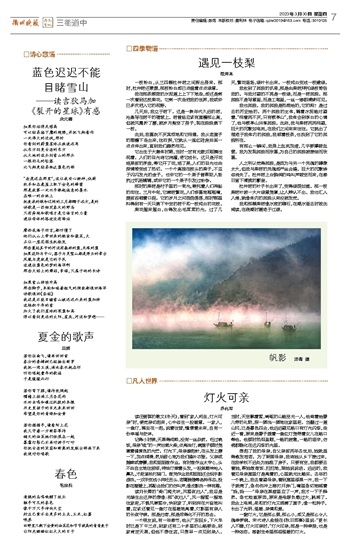灯火可亲
乔兆军
读汪曾祺的散文《冬天》,看到“家人闲坐,灯火可亲”时,便觉亲切起来,心中忽生一股暖意。一家人,一盏灯,围坐在一起,说着往昔,憧憬着未来,自有一份幸福与安详。
记得小时候,天黑得纯粹,没有一丝杂质。吃过晚饭,母亲“呲”的一声划燃火柴,点亮油灯,满屋子顿时笼罩着橘黄色的光芒。灯光下,母亲撩起针,在头发上擦一下,加点润滑,然后耐心地为我们缝补衣服。父亲或搓麻或磨镰,我和姐姐做作业。有时做作业太专心,头不由自主地往前倾,待油灯燎着头发,一股焦糊味呛入鼻孔,才赶紧拍打脑门。做完作业我和姐姐还会玩手影游戏,一双手变成小狗吐舌头、老鹰展翅等各种形态,投影在墙壁上,再配合我们的仿叫声,像皮影戏一样有趣。
读刘长卿的“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我总是无端生出这样的想像:那“夜归人”,风一程雪一程地往家赶,不惧风寒雪冷,快到家了,听到狗在兴奋地叫着,应该还看见一盏灯在温暖地亮着,灯影里有亲人的长夜守候。那是归宿,那是浓得化不开的思念。
一个朋友说,有一年春节,他从广东回乡,下火车时已是下午三点,到家还有二十多里的山路要走,到家肯定天黑,但他不想住店,只想早一点见到亲人。当时,天空飘着雪,崎岖的山路空无一人,他背着给妻儿带的礼物,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家里赶。当翻过一道山冈,已是暮色四合,他远远望见路口有灯光闪烁,走近一看,原来是妻子提着一盏红灯笼带着女儿在路口等他。他顿时热泪盈眶,一路的疲惫,一路的艰辛,仿佛都融化在这闪烁的光里。
想起了我的母亲,自父亲前两年去世后,她就显得愈发苍老。为了照顾母亲,我将她从乡下接过来,在我学校不远处为她租了房子。只要有空,我都要去看她,帮她做做饭、扫扫地,陪她说说话。远远的,我看见母亲屋里灯是亮着的,心里就无比踏实。去年的一个晚上,我去看望母亲,看到屋里漆黑一片,我一下子就慌了,急匆匆冲上楼打开房门,嘴里急切地喊着“妈,妈……”母亲在黑暗里应了一声,我才一下子释然。急忙检查原因,原来是电源负载过大,跳闸了。我合上电闸,柔和的灯光又洒满了屋子,像一粒种子,长出了光明、温暖、亲情和爱。
一窗灯火,它是那么弱,那么小,却又是那么令人魂牵梦绕。宋代诗人俞桂在《秋日即事》里说:“更长人不睡,灯火可亲时。”灯火可亲,那是一种牵挂,也是一种依恋。感谢生命里那些温暖的灯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