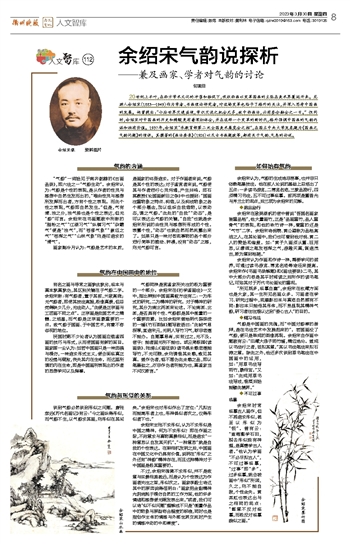余绍宋气韵说探析
——兼及画家、学者对气韵的讨论
何雨菲
20世纪上半叶,在西方学术文化的冲荡和推促下,吸收西画以变革国画的主张在美术界蔓延开来。龙游人余绍宋(1883—1949)作为学者、书画理论研究者,对这场变革也给予了格外的关注,并深入思考中国画的发展。他曾提出:“今后世界交通益便,学识交流之机会尤多,故中西画法,必有参合融会之一日。” 但同时,余绍宋对中国画的历史和精髓更有着深切体会,并在这样一个变革的新时代,格外强调中国画的气韵内涵和独有价值。1937年,余绍宋“承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之招”,在国立中央大学发表题为《国画之气韵问题》的演讲。其撰著的《画法要录》(1926)以及古书画题跋等,都有关于气韵、气息的论说。
气韵的内涵
“气韵”一词始见于南齐谢赫的《古画品录》,即六法之一“气韵生动”。余绍宋认为:气韵是个性的表现,是从作者的性灵与感想中自然生发而出的,“唯由性灵与感想所发挥而出者,方有个性之表现。而此个性之表现,气韵即自然发生。”但是,气有清、浊之分,浊气虽也是个性之表达,但无“韵”可言。余绍宋在书画题跋中所称的“脂粉之气”“江湖习气”“纵横习气”“杂霸气”便是“浊气”,而“苍郁气象”“豪迈之气”“苍浑之气”“山林气象”则是可追求的“清气”。
画家陶冷月认为:气韵是艺术的本质,是画家的终身追求。对于作画者来说,气韵是其个性的表达;对于鉴赏者来说,气韵使其与作者进行心灵沟通,产生共鸣。邱石冥教授《论国画新旧之争》中也提到:“国画注重物象之特点、构造,以及构成物象之各个部分概念,加以组织自我造物,以表动态,谓之气韵。”此处的“自我”“动态”,是可以表达出气韵的关键,“自我”也就是余绍宋所说的由性灵与感想所形成的个性。表露个性,“动态”也就自然而然流露出来了。如果只是一味对客观事物的各个部分进行简单的描绘、拼凑,没有“动态”之感,则无气韵可言。
气韵在中国画中的地位
有名之画与寻常之画孰优孰劣,临本与真本孰真孰伪,其区别关键在于气韵二字。余绍宋称:有气韵者,置于其前,兴致高涨;无气韵者,即使其技法高超,极像真景,但总觉得缺少几分,无法动人,“此便是正宗画与工匠画不同之点”。正宗画是我国艺术之精髓、之结晶,而气韵是正宗画最重要的一点。故气韵于国画、于中国艺术,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
民国时期不少论者认为国画应借鉴西画的技巧与形式,从而使国画有新的面目。画家顾一尘认为:如若中国画只是一味因袭与模仿,一味追求形式主义,便会面临真正的没落与腐败,丧失其内在生命。而这里所谓的内在生命,即是中国画所表现出的作者的思想学问以及胸襟。
气韵同样是赏鉴家所关注的极为重要的一个部分。余绍宋在《初学鉴画法》一文中,指出辨别中国画真假方法有二:一为形式的研究,二为精神的研究。对于精神的研究,其分为南北两派来论述。不论南派、北派,是否具有个性、气韵都是其中衡量的一个重要因素。比如余绍宋曾给明代陈洪绶的一幅《竹石图轴》题写跋语曰:“此帧气息深厚,直追宋元,无明人写竹习气,断非老莲不能办。自题摹息斋,实有过之,无不及。信乎!能者固无所不能也。或云周栎园《读画录》、张浦山《画征录》诸书俱未载老莲能写竹,不无可疑,余则谓惟其未载,愈见其真。盖作伪者,恒不愿伪此未载之品,即以笔墨验之,亦非作伪者所能为也,真鉴家当不河汉斯言。”
气韵与形似的关系
谈到气韵必然谈到形似之问题。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有云:“今之画纵得形似,而气韵不生,以气韵求其画,则形似在其间矣。”余绍宋也对形似作出了定位:“凡拟古而能离形者上也,形神俱似者次之,仅得形似者下也。”
余绍宋主张不求形似,认为不求形似是中国之精神。何为不求形似?即在作画之际,不刻意求与真物真景相似,而是追求“一种意思以自发其天机”。“一种意思”就是自我的个性表达。在照相机发明之后,中国画在中国文化中仍具有价值,说明在“形似”之外还有“神韵”精神存在,而且这种精神对于中国画是极其重要的。
不过,余绍宋强调不求形似,并不是故意与实景相差甚远,而是认为个性表达为作画者关注之首,形似次之。画家李毅士将这其中的原因说得很明白:“画家把全副精神光阴消耗于模仿自然的工作方面,他的许多情绪和感想便无暇发表出来。”或者,我们可以将“似不似问题”理解成不只是“衡量作品中的物象与原型吻合程度的标准,同时也是指创作主体的情感与外部世界交流时产生的情感冲动的中和律度”。
如何始有气韵
余绍宋认为,气韵的生成绝非易事,也并非只依赖笔墨技法。他在前人论说的基础上总结出了五点:一多读书游览,二博览名迹,三敦品励行,四须精习书法,五不可过事临摹。前两项是董香光与芳兰士的观点,后三项为余绍宋的见解。
◆敦品励行
余绍宋在致吴湖帆的信中曾说“吾国名画家皆重品格”,他大量画竹,正是“品画重竹,品人重骨气”的表现,和他的咏竹诗一样,看重的还是“气节”二字。余绍宋将倪瓒、黄公望称为品格高洁之人,在其论画中,我们也可看到他对倪、黄二人的赞扬和偏爱。如:“黄子久画须从董、巨用思,以潇洒之笔发苍浑之气,游趣天真,复追茂古,斯为意到格随。”
余绍宋认为作画和作诗一样,需要学问的滋养,可通过读书游览、博览名迹等途径来提高。余绍宋作《书画书录解题》和《画法要录》二书,其中大部分内容是其平时阅读之后所作的读书笔记,可知其对于历代书论画论的重视。
“所见既多,临摹自富”,余绍宋在收藏方面也是大家,其一生所见名画众多。习画者在学习、研究过程中,观摩影印本与真迹自然颇有不同:影印本只能传其形体,而不易显现其精神气韵,研习者往往难以达到“委心古人”的目的。
◆精习书法
气韵是中国画的灵魂,而“中国对韵律的崇拜,是在书法艺术中发展起来的”。若国画没了气韵,便只是单纯的图像再现。余绍宋自作画中题跋有云:“旧藏大涤子雨竹幅,精迈绝伦。盖纯以书法行之者,兹拟其意。”其以书法笔法来拟石涛之意。除此之外,他还多次谈到草书笔法在中国画中的运用,如:“用草书法写雨竹,最相宜。”又如:“此纯用草书法写成,惟酒后始能臻此境界。”
◆不可过事临摹
余绍宋时常临摹古人画作,但不再追求形似,甚至以形似为“恨”。曾有云:“查梅壑学石田,脱去形似独有神理,是真善学古人者。”他认为学画“不必尽拟古人”,不可过事临摹,“过事”即“多”。过多临摹,就会被画中“形似”所困,久之,则不能自拔,个性全失。黄宾虹也表达出与之相同的观点:“鄙意不反对临摹,而极反对临摹貌似之画。”